
视听时代影视剧带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时间:2025-07-30作者:admin浏览: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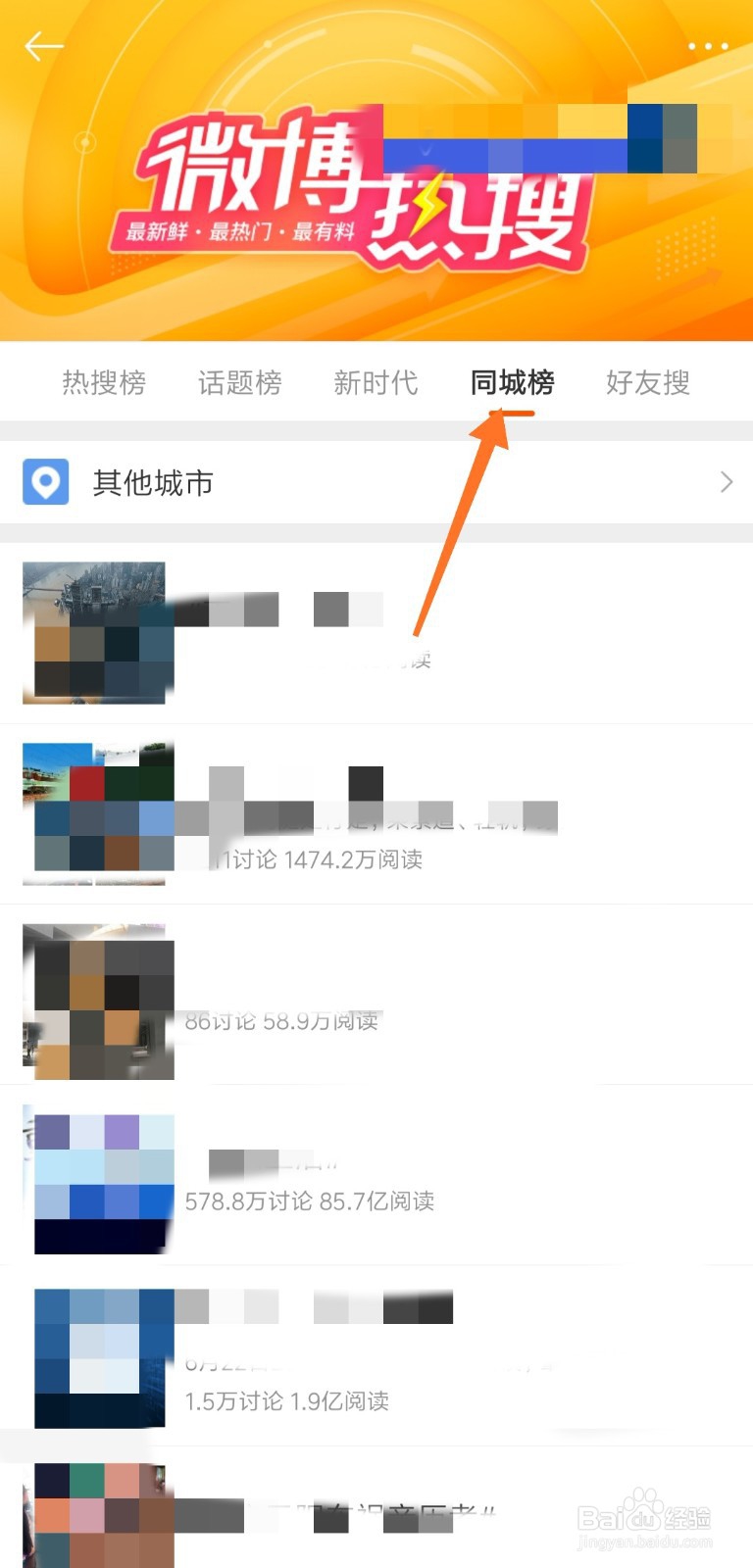
影视旅游(Movie Induced Tourism)指依靠影视带来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产生观众旅游动机并带动当地旅游产业。近几年,影视剧对地方文旅效应的带动效益明显,“影视+文旅”的模式也在多个案例中被广泛实践和验证。通过故事讲述、场景设置以及拍摄方式,影视剧以强大的视听艺术感染力激发出观众对拍摄取景地的实地体验欲望,因此带给地方相应的流量,完成文旅消费转换。同时,相关部门也逐渐加大对文旅的扶持力度,助力“影视+文旅”成为强劲风口。2022年8月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1]2024年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印发了《关于开展“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的通知》提出2024年创作播出100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主题优秀微短剧。[2]纵观当下,“影视+文旅”的热潮已然来袭,将文旅元素融合在影视剧的形式广泛发展,而影视文旅产业的融合也成为当下的时代话题。在视听时代下,影视剧如何更好地带动地方文旅发展?“影视+文旅”如何实现相互成就、相互赋能?我们需要从影视剧角度,探讨影视剧带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一种理论。它先被味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3]也就是说,作者的再创造是在大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两个文本或是两个艺术种类之间具有某种连接,观众或读者在观看以及阅读中产生一种闪回式的体验,唤起某种关于记忆的情怀。
随着文旅元素在影视剧中的占比增多,两者的融合也越发自然,“影视+文旅”也成为高频讨论词。影视业作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其文化和思想的传达对大众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文旅则是将文化和旅游融合,在旅游形式中进行文化输出。影视和文旅两者的内核都是文化,为“影视+文旅”的产业融合提供内容基础。[4]同时,两者具有一定的互文性。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影视+文旅”的互文运作机制能延长影视业产业链,对影视行业发展新格局的构建和新蓝图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在运作机制中也能在为旅游地提供宣传推广作用,实现经济持久化发展。
影视剧和地方现实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空间介入到影像中,构建出真实的、源于生活的画面,以一种复现的方式渲染影视剧创作的真实底色。同时,在日常叙述以及充满生活气息的镜头中,增强影视剧的世俗性,观众更能沉浸于艺术编织的日常世界中。影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以云南大理的云苗村作为取景地,在这一远离城市的乡村空间中生活着一群可爱的人,过着朴实的田园生活。“彩云之南”的自然景观和生活气息赋予影像田园牧歌式风格,让该剧具有治愈人心的效果。黄河路作为地理空间对上海形象传播具有重要作用,也代表着上海一个时代的城市文化。《繁花》让各色人物集中在黄河路上,呈现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希望与绝望,人物的命运起伏和整个时代变革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该剧主题的丰富性。其次,影视剧也如镜像般反映现实,促进观众对现实的了解。影视剧中的思想厚度、表达温度以及思考锐度深层次呈现地方文旅,引起观众同频共振,形成情感链接并引发线下实地体验欲望。如《去有风的地方》将距离云南大理还有七八公里的小村庄展现在观众面前,通过影视剧我们了解到地方人文风貌和中华传统文化,感知到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云南。《我的阿勒泰》展现了阿勒泰深厚的民族风情、民族文化底蕴,叙事中那些宏大意识在草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中体现。镜头聚焦在该地生活的鲜活的、当下的个体,让该剧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大众性,迸发出一种难以抗拒的活力,使阿勒泰的优美风光、有趣人文深入人心。影像的传达促进当地的旅游经济,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观众去到地方进行实景体验和文旅消费之后,影视剧更加具有生命力,线下反哺线上的长尾效应更加显著,真正实现影视和文旅的双向奔赴。
此外,从深层逻辑分析,影视剧和现实的互文运作在本质上也是符号生产和占有问题。影视剧不仅让观众具体感知到地方风貌,还会生产出符号意义,推进观众对地方的符号想象,刺激消费者产生需求。如《去有风的地方》和云南大理的互文实质是对自由符号的生产,具有逃离都市、放松身心的主题。《我的阿勒泰》和阿勒泰的互文实质是探索符号的生产,是对远方世界的向往和探索。符号的生产让观众意味自己需要某种产品,使其对符号进行追逐和占有,也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视听媒介是当今文化表达的重要手段,影视剧以特殊的视听形式和叙事方式,在剧情、美术、拍摄等元素中植入地方文化特色,让地方风土人情得到更为具体、丰富的展示,提升了地方景观和文化的能见度和被感知度。同时,影视剧和取景地形成互文,观众对取景地产生形象感知,认识到该地的民情风貌,产生寻求体验的旅游冲动和消费热情,从而实现文化空间的扩容,或者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也由此实现从观众到游客的转变。王家卫导演的影视剧《繁花》成为现象级作品,不仅取得高收视率和讨论度,“繁花热”也从线上延展到线下。剧中的重要叙事空间“黄河路”成为网红打卡第,上海特色美食“排骨年糕”也重新走红,更是推出了“宝总泡饭”“繁花套餐”。《去有风的地方》让凤阳邑村的“有风小院”成为一个文旅品牌,整个村也在文旅项目带动上增加了更多就业机会。
影视剧播出的热度对线下文旅和地方经济能够产生巨大影响。数据显示,《去有风的地方》开拍前,取景地游客日流量小于20人。两年后剧集播出,当地日均旅游人数呈几何级增长。时常呈现人山人海、一房难求的兴旺景象。《我的阿勒泰》中北疆的草原、雪山和旷野等让无数观众向往,也带动阿勒泰旅游市场的火热。在《我的阿勒泰》开播之后,阿勒泰旅游度假产品的预订量环比前一个月同期增长超370%,带动阿勒泰地区旅游人数同比增长80%+,旅游相关收入同比增长90%+。
讲好中国故事是文艺作品创作的基本需求和责任,在时代变革中讲述什么故事、塑造怎样的人物、进行怎样的价值表达都是创作者们需要考虑到的。影视剧作为艺术媒介对生活、时代以及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映。文旅题材影视剧选取了不同的地方空间作为故事的叙述背景,强调地域人文地理特色,并在故事讲述中深度挖掘、细腻展现各地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历史底蕴和生活方式,让观众在观看中沉浸式感受地方魅力,产生旅游兴趣和向往之情。在影视剧《繁花》中导演塑造出多位出色的人物形象,拍摄出高级有质感的影像画面。但整部剧中,所表现的核心点始终是成长中的上海城市。该剧从剧本、美术、人物塑造等环节都围绕上海展开,拍上海景、说上海话,让上海在剧中保持高出镜状态,体现出上海的时代精神,也唤起观众对上海的关注和消费热情,成功带动上海文旅发展。如串联起整个故事的黄河路、外滩27号等地标,人物说的沪语方言等。此外,上海美食也渗透在《繁花》中各处的画面和台词中,有6碟小菜的上海泡饭,上海本帮菜、排骨年糕等。本地美食不仅体现出上海的饮食特色,也暗示着人物关系,推动剧情发展。黄河路上繁华饭店和上海市井小店的饮食文化也融入到人物命运和此起彼伏的时代画卷中。
另一方面,将文旅与影视剧相融,在影视剧中传达地方性、民族性传统文化、非遗技艺是推动地方文旅优质、长远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影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在云南大理取景,这里也是少数民族白族的聚集地,该剧便将视线聚焦到当地非遗文化,带领观众关注白族刺绣、白族扎染、剑川木雕等非遗文化和技艺。这些非遗文化的呈现和突显也为当地后续的文旅产品开发提供元素,刺激大众对非遗文化传承的兴趣。
影视媒介通过故事叙述和视听技术对取景地方空间赋予多意性呈现和表达。观众在对拍摄地感兴趣后主动去往地方并寻找影视剧中的场景。大众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也从被动向主动转变。而影视媒介在展现取景地空间时经由影视文本、美术置景等多方面的建构,具有现实与虚拟两重属性。同时,观众在看完影视剧中的空间后,对其进行文化想象、意义构想,产生第三重精神空间。因此,影视对地方空间不止是简单再现,也是创作者和观众的编码和解码,在这过程中一起对空间创造性再建。
真实地域文化与艺术再现表达反映出不同作者对城市的空间想象和文化追求。王家卫导演通过视听语言艺术手段为事实染色,给予影视剧《繁花》独特的印象和色调,细节真实性和叙事想象性也让《繁花》游离于客观存在与主观再现之间,赋予上海城市隐形张力并形成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繁花》并没有使用纪实拍摄手法还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上海地域生活,而且王家卫导演所展示的上海不太像人们记忆中的上海,反而更偏向于传统中的香港影像,是导演对自己记忆中的上海的艺术再现。“将单个的空间,定位于关系领域中,并将空间的意义置放在这种关系中,这就是现代城市结构部署的一个独特特征。”[5]该剧的主要取景地是上海黄河路,该地方是传递城市文化的物理空间,也承载着上海人的情感和记忆。在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创造出独特的生活体验并形成群体身份认同,最终成为空间记忆媒介。王家卫在《繁花》中将上海黄河路这一地方空间进行编码,观众在观看中对黄河路进行解码,通过自己的主观认知和空间想象,赋予黄河路空间精神意义。观众通过影视剧《繁花》认识到黄河路,并通过作品视听感受到城市的生活节奏和氛围,体验地方的文化底蕴。
当下IP(intellectual Property)影视剧在收视率、讨论度上都接连突破新高,受到年轻人的追捧。“IP热”也形成了新的市场竞争模式。一个优质的IP能提供多元化原创内容的开发可能性,而且可以延展到不同的产业领域。在一部优秀影视作品受到观众的欢迎和信赖时,所取景地方空间的文化内涵也会随着作品影响力增强而树立起长久性的文化品牌。
“空间是人造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是各种利益奋然角逐的产物。它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空间从来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过程而保有一个自主的地位,事实上,它是社会的产物。”[6]“影视+文旅”的融合增强了旅游地业态多样化发展,形成多元盈利模式。随着影视剧热度的提升,地方旅游业意识到其潜在价值,建设地方IP品牌,赋予地方特色文化、历史和意义,增加文旅附加值,推进具有特色调性的地方IP落地。
文旅在影视的拉动下,使优秀IP的文旅价值获得广泛认同,从线上种草到线下引流,产出高热度出圈案例。影视剧《人世间》播出后,政府将剧中的一百余个主要取景地进行统筹分布,提取其文化内涵,打造旅游新地标,描绘出《人世间》影视文旅打卡地图,构建起吉林影视文旅IP生态圈。陕西西安以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为切口,打造出“长安十二时辰”街区,推出“热门剧集+沉浸式娱乐+主题餐饮+国潮产品”新消费综合体,游客沉浸式跟随主人公张小敬去守护长安。
文化认同是建构在群体对于某种思想、道德和价值观上的精神归属意识。影视剧在影视技术基础上对故事内核和其背后价值观的传播能够赋能文化旅游。与之相对应的是,游客对文旅的文化认同也能带动影视作品的创作、传播和消费。
影视剧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旅游期望的生命周期曲线也会随着剧从开播到播完的时间推移而显著下降。因此,影视剧维持地方文旅长期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赋予其文化价值,使其具有长远的吸引力。通过影视剧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差异化物质形态空间,唤起与大众的共同文化记忆并引起文化认同,以期延伸观众的消费热情,形成“影视+文旅”在多维度上的良性互动。
影视文旅产业是影视、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产物,在挖掘乡村文化、扩宽乡村行业边界、带动乡村经济及文旅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对标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影视文旅产业的开发实现乡村产业多格局发展,为产业注入活力,使当地农民增收、创收有新的可能性。文旅题材影视剧创作可以结合时代环境和社会文化议题,让其具有可看性的同时兼具社会意义,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主流价值观。影视文化融入乡村不仅能传播乡村传统文化,也能将现代科技技术带到乡村,为当地带来新的思想和观念,传统乡村农耕文明、非遗文化等通过影视文旅产业迎来新生,不断助力推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而观众对影视剧思想文化传达的直观感受也代表着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思想认同。
《去有风的地方》便是聚焦乡村振兴议题,在温暖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中以小切口对美丽乡村图景进行真实再现,在个体与时代的共同发展中,唤醒人与乡土的情感勾连,成为乡村振兴时代议题的鲜活注脚。该剧以都市女孩许红豆来到大理云苗村排解忧郁心情为叙事主线,在弱化叙事冲突,呈现闲适田园乡村生活中给予观众精神治愈。此外,该剧还通过一个个具有生活气息的普通人物故事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议题基础上探讨了留守儿童、非遗传承等主流话题,在烟火气氛围中将故事娓娓道来,观众小人物的人生命运,传递善良人性和幸福感生活,极具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
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与情感的载体,影视剧对空间的塑造增强了地方的独特性,也将属于人物个体的回忆上升为一个群体共享的集体记忆。影视剧中的特定取景空间构筑成城市的集体记忆,通过人物在空间中的经历唤起观众对这一区域的印象和记忆,甚至是归属感,个人与他者的记忆重合唤起更多人的共鸣,更是在被社会客观化后形成一种公共符号被特定群体共享。
从内容层面看,影视剧的题材、叙事以及人物可以从历史逻辑和文化内涵出发,深入挖掘和探讨集体记忆。对时代往事的唤醒成为现代人的一种重要沟通方式,影视作品通过书写往事引起观众的身份认同,并借由文化记忆带来符号式消费热潮。集体记忆中暗含着城市差异性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符号,具有自身的独特内核。通过集体记忆打造城市文化原创IP能快速建立起人们对城市的差异化认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特别之初,并吸引前来旅游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王家卫导演通过拍摄《繁花》展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风云际会背景下的上海都市往事,呈现那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下无数个体的追梦之路。《繁花》的播出也激活了观众对于上世纪老上海的深层次心灵感知,通过阿宝、汪小姐以及黄河路上各色人物故事形成时代缩影,也和观众建立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并达成共识和共情,构筑了群体对上海的集体记忆,这也有助于沪上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影视剧在叙事情节和环境氛围的渲染下获得观众精神上的关联性和认同感,受众与影视媒介建立情感连接,观众从中获取到精神栖息地,得到愉悦和能量,更是对生活增添了憧憬和期望,之后将这种情感投射到现实空间中激发观众产生旅为。观众通过影视剧对地方文化特色的反映,对此感到精神认同,在这一认同基础上扩大想象空间,拓展时空渠道,最终满足观众对文化旅游的多种精神需求。
《我的阿勒泰》非常符合网生代年轻人对新疆本地生活的想象,让人以当下的眼光来感受新疆,感受新疆的宁静、美好和孤独,和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具有治愈的效果。都市空间的部分年轻人处于一种精神困境中,急需精神慰藉。《去有风的地方》抓住这一问题,在主人公许红豆逃离都市揭开心结感悟生命意义的人物故事中表现云南大理的自然风光,洱海的风、古城的景、古镇的路汇聚成的惬意田园生活以乌托邦小镇的形式带到大众视野中,成为缓解社会个体压力的精神解药,并将大理空间赋予远方、美好、诗意等意义,让观众从繁杂现代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短暂脱离。乡土自然风光和缓慢的生活状态和深居城市的都市生活节奏产生一定的审美距离,这一距离引发观众对当地的无限遐想,将想象中的美好风光都投射到云苗村中,形成影视剧与受众想象的二次创作,也赋予了影视剧新的生命力,创作者和观众共同为这一地方建构出了一个美好乌托邦,让观众在自然之中寻求人生、探寻自我。
影视剧是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着多重社会功能和人文价值。在现代化社会影视剧创作中,需要考虑受众的多样化需求,这要求创作者要打破传统的、单一的惯性思维,激发影视剧创作的无限可能性,和其它领域实现多元融合。“影视+”背后的无限可能是中国电视剧高质量、精品化发展的良好印证,也是影视剧满足人们群众精神文明生活的重要方式。影视与文旅的结合打造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影视作品,这一融合不仅能提升影视产业和文旅产业的发展,实现1+12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能在跨界融合中传播当地文旅特色,推动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让中国文化资源焕发光彩。
【本文系成都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都市交通+旅游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基地2023年度重点项目《文旅融合视域下“影视+旅游”产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31004)研究成果】



